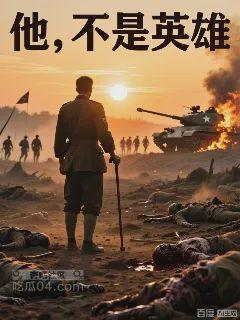- [ 免费 ] 前言
- [ 免费 ] 第一章
- [ 免费 ] 第二章
- [ 免费 ] 第三章
- [ 免费 ] 第四章
- [ 免费 ] 第五章
- [ 免费 ] 第六章
- [ 免费 ] 第七章
- [ 免费 ] 第八章
- [ 免费 ] 第九章
- [ 免费 ] 第十章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三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四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五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六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七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八章
- [ 免费 ] 第二十九章
- [ 免费 ] 第三十章
- [ 免费 ] 第三十一章
- [ 免费 ] 第三十二章
- [ 免费 ] 第三十三章
- [ 免费 ] 第三十四章
- [ 免费 ] 第三十五章
- [ 免费 ] 第三十六章
- [ 免费 ] 第三十七章
- [ 免费 ] 第三十八章
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-AA+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
繁
第二十九章
2018-5-26 06:01
(9)美丽的西藏
早已进入美丽的西藏界内了,只是一直没遇见藏民。迎接他们的只是雪山、原始森林、四不象、大野牛、冰河等,他们期盼着见到藏人。
他们已经疲惫不堪,多数人已没个人样了,像野人一样。到达目的地了,他们不由得想到那些永远地留在路上的人。那些人要是在该多好啊。
他们走过了人类未成走过的而且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路,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。
出发时,他们一人配三匹壮马。现在,已基本无马可用了,仅存的少数几匹,只能是给重伤病员换着用。他们是先头部队,此时此刻还无暇顾及风景,他们要先设法建好联络站,做好对后序部队的接应。
[近年来,看到一影片的简介,讲述进藏的一个先谴连命运的颇折。没听他说他是不是进藏先谴连的,但听他说他进藏时的那些故事却是在探路,而且是在走前人未走过的路。]
一天清晨,听见几声羊叫。是野羊?他们纷纷起身。
啊,是名牧童和几只羊。他们仔细牧童的穿着打扮,又拿着照片作对比,再用藏语寻问。
“没错,是藏民!”
他们之所以很谨慎,也是怕这样没日没夜的行军多日,那弯弯曲曲的行军路线早让人很疲劳了,会不会弄错地方而跑出国啊?看着眼前的藏族牧童他们可以确定,他们还在在国境内行军。
藏族牧童和几只羊都直愣愣或者说是傻呆呆的看着他们,那神情像是在问:你们是从天上来的吗?
经藏族牧童指引,他们见到了更多的藏民。
他们的苦没白受,他们终于到了——美丽的西藏。
随着进西藏深入,见到了传说中的藏族民俗。
藏民也更加好奇地看着他们,在藏民眼中,他们更像是一群从天而降的什么,其中有的可能还在怀疑他们是人吗?一见他们就跑,在后藏的藏民基本是没见过藏民以外的人。
他们带有翻译,送上礼物,与藏民作了沟通,全面介绍了政策,解了藏民的各种习俗,并向部队所有人传达。经过喇嘛庙时,他们每人还要转一下原来只有藏民才转的轱轳,也算是敬神?河里的鱼很多,小狗都能很轻而易举地逮住吃,但他们是不能去打捞着吃的。天空中的老鹰是藏民心中的圣,绝对不能打。还有天葬习俗等等,他们要尊重藏民的习俗。
那时的藏民有病基本是不看医生的,宁肯信喇嘛。为藏民看病很艰难,医生反倒要费尽心机地去说服藏民,但他们还是在努力的去做。
不久,收到了前藏部队发来的电报,他们派出了联络员。与前藏过来的部队会师后,进军西藏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一些事
他曾养过的一条军犬
他没说过他是怎样得到那条军犬的,但他在西藏时,确实养过一条让他十分难忘的聪明能干的军犬。他给8、9岁的儿子专们讲过这条军犬的故事。
这条军犬是条品种很纯的狼犬,个头挺大,不熟悉的人看着会觉得那军犬凶巴巴的。军犬原来就受过训练,他又常常训练它做些日常事,久而久之它竟然能替他办些事了。
他特别做了一只小挂篮,挂在军犬的脖子上,军犬还能代他去食堂打饭菜。军犬还懂得排队,但谁也不敢加它的队,都得让它三分这条军犬只认他,不熟悉的人是不能摸它的,轻者以吼声警告,重者一般还没发生过。
这条军犬在他的带引下还常常给大伙做些表演,逗的大伙笑的很开心。他喜欢一个小滩上的熟肉,每次去买时都带着军犬。他给卖熟肉的滩主讲好了,试着训练了几次,这条军犬竟然也能单独完成买熟肉的任务了。同样地,谁也不敢抢它买的熟肉。
此外,这军犬还懂得陪哨兵站岗,哨兵们也很喜欢它。
一天,来了名副团,怎的就一眼看上这条军犬。副团想驯服它,就去强行抓住它摸它,这可犯了大忌,它怒吼一声,反身一口将那名副团的手咬住,副团拼命地挣脱。副团也是打过仗的,皮气比那军犬还差,见军犬不认副团大人倒也算了,还敢咬?副团十分恼怒,拔出一种加拿大产的大口径手枪连续几枪。
子弹穿过军犬的好几处要害。军犬倒在了血泊中,它努力地想站起来,但已经做不到了。
军犬圆睁着眼,尽管对这个世界带有无限的眷恋,但还是走了。
看大门的哨兵平时也很喜欢这军犬,因为,军犬晚上常常来与他们一起站岗,给他们壮胆。哨兵与他的关系也很好,同时也不知道团副是什么人,听到枪声赶过来一看,立刻把团副抓住,大声喝斥。
藏北指挥所所长
是他的运气好?应该是他很勤奋地工作,去西藏后,他曾经担任过藏北指挥所所长。他的个性是积极进取的,做事总是向好的方向做,从不坑人。或许,这也是当时上级看中他的一个优点吧?才把西藏这样地方的差事交给他们。
藏北指挥所所长是个什么级别的官,应该能从中共的西藏史志或新疆南疆军区的一些档案文件上查到。从他讲到的一些事可以断定,藏北指挥所所长可能没什么级别,几个去西藏的汽车团长却还得常常求他照顾一下物质上的供给。况且,后藏也只有一个藏北,藏南还被印度人占着。
在群众运动中,当一些疯狂的人们质问他做反动军官做过什么坏事时,他曾用在西藏做过藏北指挥所所长作为“护身符”。孩子们在读书时,因填写家庭父母亲的出身的问题而感到尴尬时,他曾让填写他曾经是藏北指挥所所长。
藏北指挥所所长,应该算是他走到了他军旅生涯的巅峰。
永远的军人
57年,应该是在西藏叛乱前的几个月吧,他转业到地方单位当了一名普通医生,结束了他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。
他以转业军人的身份到地方的,常常是默默无闻地想法为大家做些好事,从不与人争什么。他从未谈他的转业的原因,他的转业应该是令他伤心的,感到他总认为他应该是名军人。到八十年代,他有次突然心血来潮地做了套军绿色的军便服,说是自己曾经是名军人。他的服装即便是其他颜色的,也是军便服的样式,而不像很多人那样穿中山装。
半大的儿子虽不理解,但也习惯了他总是云里雾里的个性。其实,他还是怀念他的军人时代。三十年的军旅生涯,占居了他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。青年时代,是血与火交融的青年时代,一个真正的光荣的时代。中年时代,向新的领域进军。
他的心里,他永远是个军人。
与一群恶狼打了一夜
他去的是一个由数字编号的工程队,这样的单位一般是属国防上的,其组织机构和编制像部队,但工作性质又与地方单位是一样的。
那时,大的工程队下设几个小工区,因工程队配制的医生少,因此,他常常需要在几个工区间跑。距离近的一般是靠步行,距离远的则骑马。单位考虑他常常是一个人步行,故考虑申请一支驳壳枪让他带着,但因每次出诊时,带的药品较多,故没要单位申请的驳壳枪。驳壳枪加子弹有一斤半,带着重量增加了不说,况且他已不是军人,带枪在很多时候会增添不少手续上的麻烦,实在是不值得。医生太少,合格的就他一人,本身就忙不过来,他想将主要精力放在治病救人上。
一天黄昏,他动身赶往另一个工区就诊,想为第二天多争取一些时间,这却让他历经了一次危险。
两工区相距约二、三十里远,他与对方的工区取得联系后,背着一医疗箱出发了。
他是步行,随身挟带的除了医疗救护箱外,他还拿了根一米来长的短棍。他出发后不久,天色就黑了下来。快走到两工区之间时,他感到身后有什么在跟着。他回头用手电照射后,看到几十双闪着绿光的眼睛——是一群狼。
他镇定了一下,迈着稳健的步伐走。此时,他十分留意身后,还不能惊慌,一慌狼群就会扑上来。
那群狼开始是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三、四十米的地方,他走狼也跟着走,他停狼也跟着停。随着夜深,那群狼的胆子大了起来,越跟越近。
狼群距他十几米时,他时不时地用石块投向狼群,狼群见状会停一下。慢慢地,石块的打击不起多大作用了,个别的狼开始试着围上来,准备攻击了。
他终于与那群狼接火了,他开始是连喝带打地,边打边走,且只打冲在最前的几只狼,不与狼群缠斗。到后来,那群狼见他的体力有所降低就围着他攻击。
他还是边打边冲,短棍还常常被狼咬住,不知不觉中,短棍打坏了,只剩一尺多长。他不能再保护药品了,就将医疗箱取下,将里面的器具分别砸向进攻的狼。医疗箱打碎了,他将武装带(扎在腰间的宽皮带)取下来配合着剩下的短棍打。到黎明时,只剩下一条皮带加石块了。他与狼群整整“战斗”了一夜。
天边稍稍发亮了,狼群见他很顽强,似呼也有点忧郁了,对他的攻击也减弱。他也快支持不住了,据他后来说,他最多还能坚持一小时了。
单位派出的两位持枪的接应人员及时地赶到了,开枪击毙几只狼,将狼群驱散。
他,脱险了。
自行车
儿子童年时的记忆中,家里是有辆自行车的。而且,还是一辆加重型的自行车,前后都能带人。那时,他常带着未上学的儿子骑自行车去城里买药。
儿子很喜欢那辆自行车,一路上常常替他按铃,回家后也常常会帮忙擦洗的。虽然,儿子还不会骑自行车,但却喜欢玩自行车,如按车铃来听铃声,转着自行车的轮子再玩刹车,或是拨着辐条听响声。那辆自行车,也是儿子引以为自豪的,常常在小伙伴面前炫耀。有时,儿子玩的起兴时,也会将小伙伴带来家里玩自行车。可以这样说,那辆自行车也是儿子童年时的一个梦。
那辆自行车很辛苦,常常有人来借,他好像从来没有拒绝过,还总是笑脸相迎。
有一次,一名工宣队员将自行车借去了。还来时,只将自行车交给在院子里玩弄的两个孩子,还满脸堆笑地让两孩将自行车交给他。然后,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
儿子记忆中的那名工宣队员是很凶的,还自行车却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儿子不由得感到奇怪,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“呀,自行车车上的锁没有了。”女儿看了看自行车叫起来。
“怎么了?”他从屋里出来了,看了看自行车,又沉思了一会说:“没关系的,算了。”
原来,工宣队员将自行车借去后,把车钥匙弄丢了。那时正值文革期间,工宣队员是很红的人物,做起事来也很蛮横,就干脆将车锁砸掉了。这事要是放在一般家庭,非去找那工宣队员大吵大闹的。而他,却一声未吭。
一天,一名青工和其姐姐来到家中对他哭诉。儿子在院子里看见了,但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还是照样玩自己的。青工是名学徒工,那天将自行车借去后就没还回来,只是与其姐姐来了。
以前,儿女们听见自行车铃响就知道是爸爸回来了,而这种铃声却突然间消失了。一连好几天,没见自行车,儿子有些发慌便问女儿:“姐姐,自行车呢?”
“丢了,那天,那青工姐弟俩来就是说自行车丢失的事的。”女儿对儿子说。
“丢了?”儿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
“是丢了。”女儿对儿子说:“爸爸想算了,那青工姐弟俩才凑了几十块钱。” 女儿说的数,连自行车三分之一的价都不到。
“以后就没有自行车了?呜。” 儿子听见哭了,在儿子幼小的心里,那辆自行车就像是一种精神支柱。
“没关系的,不哭。”女儿毕竟上学了,显得懂事一些。
那时,很多人被抄家。丢辆自行车算是很平常的事了,他像是早已习惯了。当然,他也是为了一对还年幼的儿女,什么事都得忍、都很低调。
或许正是这样,他才躲过了后来的那一次次的整人的运动,使得他的家庭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太残酷的冲击。
儿子终究年幼,好是心疼那辆自行车的,心里也总是想那辆自行车,还常常在梦里梦见那辆自行车。
过来人
早已进入美丽的西藏界内了,只是一直没遇见藏民。迎接他们的只是雪山、原始森林、四不象、大野牛、冰河等,他们期盼着见到藏人。
他们已经疲惫不堪,多数人已没个人样了,像野人一样。到达目的地了,他们不由得想到那些永远地留在路上的人。那些人要是在该多好啊。
他们走过了人类未成走过的而且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路,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。
出发时,他们一人配三匹壮马。现在,已基本无马可用了,仅存的少数几匹,只能是给重伤病员换着用。他们是先头部队,此时此刻还无暇顾及风景,他们要先设法建好联络站,做好对后序部队的接应。
[近年来,看到一影片的简介,讲述进藏的一个先谴连命运的颇折。没听他说他是不是进藏先谴连的,但听他说他进藏时的那些故事却是在探路,而且是在走前人未走过的路。]
一天清晨,听见几声羊叫。是野羊?他们纷纷起身。
啊,是名牧童和几只羊。他们仔细牧童的穿着打扮,又拿着照片作对比,再用藏语寻问。
“没错,是藏民!”
他们之所以很谨慎,也是怕这样没日没夜的行军多日,那弯弯曲曲的行军路线早让人很疲劳了,会不会弄错地方而跑出国啊?看着眼前的藏族牧童他们可以确定,他们还在在国境内行军。
藏族牧童和几只羊都直愣愣或者说是傻呆呆的看着他们,那神情像是在问:你们是从天上来的吗?
经藏族牧童指引,他们见到了更多的藏民。
他们的苦没白受,他们终于到了——美丽的西藏。
随着进西藏深入,见到了传说中的藏族民俗。
藏民也更加好奇地看着他们,在藏民眼中,他们更像是一群从天而降的什么,其中有的可能还在怀疑他们是人吗?一见他们就跑,在后藏的藏民基本是没见过藏民以外的人。
他们带有翻译,送上礼物,与藏民作了沟通,全面介绍了政策,解了藏民的各种习俗,并向部队所有人传达。经过喇嘛庙时,他们每人还要转一下原来只有藏民才转的轱轳,也算是敬神?河里的鱼很多,小狗都能很轻而易举地逮住吃,但他们是不能去打捞着吃的。天空中的老鹰是藏民心中的圣,绝对不能打。还有天葬习俗等等,他们要尊重藏民的习俗。
那时的藏民有病基本是不看医生的,宁肯信喇嘛。为藏民看病很艰难,医生反倒要费尽心机地去说服藏民,但他们还是在努力的去做。
不久,收到了前藏部队发来的电报,他们派出了联络员。与前藏过来的部队会师后,进军西藏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一些事
他曾养过的一条军犬
他没说过他是怎样得到那条军犬的,但他在西藏时,确实养过一条让他十分难忘的聪明能干的军犬。他给8、9岁的儿子专们讲过这条军犬的故事。
这条军犬是条品种很纯的狼犬,个头挺大,不熟悉的人看着会觉得那军犬凶巴巴的。军犬原来就受过训练,他又常常训练它做些日常事,久而久之它竟然能替他办些事了。
他特别做了一只小挂篮,挂在军犬的脖子上,军犬还能代他去食堂打饭菜。军犬还懂得排队,但谁也不敢加它的队,都得让它三分这条军犬只认他,不熟悉的人是不能摸它的,轻者以吼声警告,重者一般还没发生过。
这条军犬在他的带引下还常常给大伙做些表演,逗的大伙笑的很开心。他喜欢一个小滩上的熟肉,每次去买时都带着军犬。他给卖熟肉的滩主讲好了,试着训练了几次,这条军犬竟然也能单独完成买熟肉的任务了。同样地,谁也不敢抢它买的熟肉。
此外,这军犬还懂得陪哨兵站岗,哨兵们也很喜欢它。
一天,来了名副团,怎的就一眼看上这条军犬。副团想驯服它,就去强行抓住它摸它,这可犯了大忌,它怒吼一声,反身一口将那名副团的手咬住,副团拼命地挣脱。副团也是打过仗的,皮气比那军犬还差,见军犬不认副团大人倒也算了,还敢咬?副团十分恼怒,拔出一种加拿大产的大口径手枪连续几枪。
子弹穿过军犬的好几处要害。军犬倒在了血泊中,它努力地想站起来,但已经做不到了。
军犬圆睁着眼,尽管对这个世界带有无限的眷恋,但还是走了。
看大门的哨兵平时也很喜欢这军犬,因为,军犬晚上常常来与他们一起站岗,给他们壮胆。哨兵与他的关系也很好,同时也不知道团副是什么人,听到枪声赶过来一看,立刻把团副抓住,大声喝斥。
藏北指挥所所长
是他的运气好?应该是他很勤奋地工作,去西藏后,他曾经担任过藏北指挥所所长。他的个性是积极进取的,做事总是向好的方向做,从不坑人。或许,这也是当时上级看中他的一个优点吧?才把西藏这样地方的差事交给他们。
藏北指挥所所长是个什么级别的官,应该能从中共的西藏史志或新疆南疆军区的一些档案文件上查到。从他讲到的一些事可以断定,藏北指挥所所长可能没什么级别,几个去西藏的汽车团长却还得常常求他照顾一下物质上的供给。况且,后藏也只有一个藏北,藏南还被印度人占着。
在群众运动中,当一些疯狂的人们质问他做反动军官做过什么坏事时,他曾用在西藏做过藏北指挥所所长作为“护身符”。孩子们在读书时,因填写家庭父母亲的出身的问题而感到尴尬时,他曾让填写他曾经是藏北指挥所所长。
藏北指挥所所长,应该算是他走到了他军旅生涯的巅峰。
永远的军人
57年,应该是在西藏叛乱前的几个月吧,他转业到地方单位当了一名普通医生,结束了他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。
他以转业军人的身份到地方的,常常是默默无闻地想法为大家做些好事,从不与人争什么。他从未谈他的转业的原因,他的转业应该是令他伤心的,感到他总认为他应该是名军人。到八十年代,他有次突然心血来潮地做了套军绿色的军便服,说是自己曾经是名军人。他的服装即便是其他颜色的,也是军便服的样式,而不像很多人那样穿中山装。
半大的儿子虽不理解,但也习惯了他总是云里雾里的个性。其实,他还是怀念他的军人时代。三十年的军旅生涯,占居了他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。青年时代,是血与火交融的青年时代,一个真正的光荣的时代。中年时代,向新的领域进军。
他的心里,他永远是个军人。
与一群恶狼打了一夜
他去的是一个由数字编号的工程队,这样的单位一般是属国防上的,其组织机构和编制像部队,但工作性质又与地方单位是一样的。
那时,大的工程队下设几个小工区,因工程队配制的医生少,因此,他常常需要在几个工区间跑。距离近的一般是靠步行,距离远的则骑马。单位考虑他常常是一个人步行,故考虑申请一支驳壳枪让他带着,但因每次出诊时,带的药品较多,故没要单位申请的驳壳枪。驳壳枪加子弹有一斤半,带着重量增加了不说,况且他已不是军人,带枪在很多时候会增添不少手续上的麻烦,实在是不值得。医生太少,合格的就他一人,本身就忙不过来,他想将主要精力放在治病救人上。
一天黄昏,他动身赶往另一个工区就诊,想为第二天多争取一些时间,这却让他历经了一次危险。
两工区相距约二、三十里远,他与对方的工区取得联系后,背着一医疗箱出发了。
他是步行,随身挟带的除了医疗救护箱外,他还拿了根一米来长的短棍。他出发后不久,天色就黑了下来。快走到两工区之间时,他感到身后有什么在跟着。他回头用手电照射后,看到几十双闪着绿光的眼睛——是一群狼。
他镇定了一下,迈着稳健的步伐走。此时,他十分留意身后,还不能惊慌,一慌狼群就会扑上来。
那群狼开始是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三、四十米的地方,他走狼也跟着走,他停狼也跟着停。随着夜深,那群狼的胆子大了起来,越跟越近。
狼群距他十几米时,他时不时地用石块投向狼群,狼群见状会停一下。慢慢地,石块的打击不起多大作用了,个别的狼开始试着围上来,准备攻击了。
他终于与那群狼接火了,他开始是连喝带打地,边打边走,且只打冲在最前的几只狼,不与狼群缠斗。到后来,那群狼见他的体力有所降低就围着他攻击。
他还是边打边冲,短棍还常常被狼咬住,不知不觉中,短棍打坏了,只剩一尺多长。他不能再保护药品了,就将医疗箱取下,将里面的器具分别砸向进攻的狼。医疗箱打碎了,他将武装带(扎在腰间的宽皮带)取下来配合着剩下的短棍打。到黎明时,只剩下一条皮带加石块了。他与狼群整整“战斗”了一夜。
天边稍稍发亮了,狼群见他很顽强,似呼也有点忧郁了,对他的攻击也减弱。他也快支持不住了,据他后来说,他最多还能坚持一小时了。
单位派出的两位持枪的接应人员及时地赶到了,开枪击毙几只狼,将狼群驱散。
他,脱险了。
自行车
儿子童年时的记忆中,家里是有辆自行车的。而且,还是一辆加重型的自行车,前后都能带人。那时,他常带着未上学的儿子骑自行车去城里买药。
儿子很喜欢那辆自行车,一路上常常替他按铃,回家后也常常会帮忙擦洗的。虽然,儿子还不会骑自行车,但却喜欢玩自行车,如按车铃来听铃声,转着自行车的轮子再玩刹车,或是拨着辐条听响声。那辆自行车,也是儿子引以为自豪的,常常在小伙伴面前炫耀。有时,儿子玩的起兴时,也会将小伙伴带来家里玩自行车。可以这样说,那辆自行车也是儿子童年时的一个梦。
那辆自行车很辛苦,常常有人来借,他好像从来没有拒绝过,还总是笑脸相迎。
有一次,一名工宣队员将自行车借去了。还来时,只将自行车交给在院子里玩弄的两个孩子,还满脸堆笑地让两孩将自行车交给他。然后,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
儿子记忆中的那名工宣队员是很凶的,还自行车却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儿子不由得感到奇怪,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“呀,自行车车上的锁没有了。”女儿看了看自行车叫起来。
“怎么了?”他从屋里出来了,看了看自行车,又沉思了一会说:“没关系的,算了。”
原来,工宣队员将自行车借去后,把车钥匙弄丢了。那时正值文革期间,工宣队员是很红的人物,做起事来也很蛮横,就干脆将车锁砸掉了。这事要是放在一般家庭,非去找那工宣队员大吵大闹的。而他,却一声未吭。
一天,一名青工和其姐姐来到家中对他哭诉。儿子在院子里看见了,但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还是照样玩自己的。青工是名学徒工,那天将自行车借去后就没还回来,只是与其姐姐来了。
以前,儿女们听见自行车铃响就知道是爸爸回来了,而这种铃声却突然间消失了。一连好几天,没见自行车,儿子有些发慌便问女儿:“姐姐,自行车呢?”
“丢了,那天,那青工姐弟俩来就是说自行车丢失的事的。”女儿对儿子说。
“丢了?”儿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
“是丢了。”女儿对儿子说:“爸爸想算了,那青工姐弟俩才凑了几十块钱。” 女儿说的数,连自行车三分之一的价都不到。
“以后就没有自行车了?呜。” 儿子听见哭了,在儿子幼小的心里,那辆自行车就像是一种精神支柱。
“没关系的,不哭。”女儿毕竟上学了,显得懂事一些。
那时,很多人被抄家。丢辆自行车算是很平常的事了,他像是早已习惯了。当然,他也是为了一对还年幼的儿女,什么事都得忍、都很低调。
或许正是这样,他才躲过了后来的那一次次的整人的运动,使得他的家庭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太残酷的冲击。
儿子终究年幼,好是心疼那辆自行车的,心里也总是想那辆自行车,还常常在梦里梦见那辆自行车。
过来人